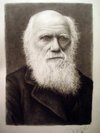
達爾文
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英語: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又譯達爾溫,是一位英國著名的生物學家、博物學家,達爾文早期因地質學研究而著名,而後又提出科學證據,證明所有生物物種是由少數共同祖先,經過長時間的自然選擇過程後演化而成。到了1930年代,達爾文的理論成為對演化機制的主要詮釋,並成為現代演化思想的基礎,在科學上可對生物多樣性進行一致且合理的解釋,是現今生物學的基石。
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使起源於共同祖先的演化,成為對自然界多樣性的一項重要科學解釋。之後達爾文《人類與動物的情感表達》以及《人類由來與性擇》中,闡釋人類的演化與性選擇的作用。他也針對植物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的書籍,在最後一本著作中,達爾文討論了蚯蚓對土壤的影響。為了表彰他傑出成就,達爾文死後安葬於牛頓與約翰·赫歇爾的墓旁,地點就在英國倫敦的西敏寺。
宗教信仰
達爾文於1876年病中執筆寫《自傳》,回顧毀譽交加的一生,目的並非出版,只是留為給子孫和妻子,所以語氣親切可人,字字出自肺腑。然而,他的兒子Francis Darwin 1887年把這本《自傳》出版了,當中有若干文字遭受刪節,部分由於害怕得罪教徒朋友,直到1958年達爾文孫女Nora Barlow才把《自傳》全文出版。註釋中的F.D.及N.B.分別指兒子Francis Darwin及孫女Nora Barlow所作的註釋。
在這兩年間1),我時常想到宗教。在小獵犬號的時候,我還是頗為相信原教義,還記得有幾位船員(他們也是原教義者)開心地取笑我引述聖經作為一些道德觀點無法反駁的權威。我以為他們開心是因為他們並未聽過這樣的論證。但這時候的我已逐漸看出不能相信舊約聖經,一如不能相信印度教徒的神聖經典或是野蠻人的信仰;舊約聖經滿是虛假的世界史,有巴別塔、彩虹作為訊號等等,以及把深藏仇恨的暴君感情歸因於上帝。我腦海時常浮現這問題,揮之不去:要是上帝現在向印度教徒顯靈,他是否會容許印度教徒將其解釋為毗濕奴、濕婆等信仰,一如基督教關連到舊約聖經。對我來說,這是全然不可相信。
進一步反思究竟要有哪些最明顯的證據,才會讓任何頭腦清醒的人相信基督教支持的奇蹟: ──我們知道越多大自然的不變規律,就越不相信奇蹟; ──我們簡直不能相信當時人們是如此無知和容易受騙; ──不能證明福音是在事件發生時撰寫的; ──福音各章的許多重要細節有分歧,這些歧義很重要,我認為這不能以這是目擊者常有的差誤就全部接納。
我提出以上反思,不是有任何新見解或價值,而是這些反思影響了我,我漸漸不相信基督教是一種神聖啟示。事實上,世上許多虛偽宗教如野火蔓延,這對我有沉重影響。新約聖經的道德規範很完美,但不能否認其完美乃視乎如何解讀一些我們現在看作是隱喻和寓言的部分。
但我非常不願意放棄我的信仰;這一點我很肯定,因為我記得時常做白日夢,夢見在龐貝古城或其他地方發現羅馬學者的舊信件和文稿,驚人地證實福音記錄的一切。我的想像力有無限空間,但越來越難以想像出可以令我相信的證據。不信任的概念雖是慢慢地發展,但終歸征服了我。改變是如此緩慢,我沒有感到苦惱,從來沒有一刻懷疑我的結論的正確性。我甚至很難想像有人希望基督教是正確的;因為聖經似乎明文表示,不信教的人們會受到永恆的懲罰,這包括我的父親、兄弟和幾乎所有我的好友。
這真是一種可咒詛的教義。2)
雖然我在晚年之前沒有太多思考人格神的存在,我在此寫下我得出的不明確結論。佩利3)稱為大自然的設計,以前我認為令人信服,如今因為發現了自然選擇定律,這些舊有論點已站不住腳。例如,我們現在已不能辯稱雙殼貝類的美麗貝鉸是由有智慧的物體所造,一如人製造門鉸鏈。生物變異和自然選擇之中的設計,似乎沒有多於風的吹向。大自然的一切是固有定律的結果。
我已在《家養動植物變異》4)的末章討論這題目5);依我所見,其中的論點至今還沒有解答。
但在忽略我們四處可見無限美好的適應性後,可能有人會質疑如何解釋這世上普遍的有利安排?誠然,有些作家深感於世上的眾多苦難,使他們懷疑如果我們只看全部有知覺的生物,究竟會有更多悲傷還是快樂──究竟這世界整體是好是壞。依我的判斷必然是快樂較多,雖然這很難證實。如果接受這結論是正確,便能符合我們從自然選擇中的預期。如任何物種的全部個體習慣地承受無限痛苦,他們不會繁衍後代,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曾經發生或是經常發生。而且有其他考慮令我們相信有知覺的生物之形成,一般是為了享受快樂。
我們相信所有生物的肉體和心智器官(除了那些對擁有者無益無害者之外)是因為自然選擇,亦即最適者生存,以及因為使用或習慣6)而形成。這些器官之所以形成,是其擁有者與其他生物競爭成功,因此增加數量。動物可以通過受苦,例如疼痛、飢餓、饑渴和恐懼;或通過享受,例如飲食和繁衍物種等等,或是兩者結合,例如找尋食物,被引導到追隨對其最有利的行動方針。任何疼痛或受苦如長期持續,會導致情緒低落和減輕行動的動力,適應得好卻能使生物保護本身免受重大或突然的禍害。另一方面,愉快的知覺可以長期持續,沒有情緒低落的效應,相反的能刺激整個體系增加活動。因此,大多數或全部知覺生物是以這樣的方式通過自然選擇而發展,所以愉快的感覺成為習慣的指引。我們為盤中飧費盡力氣和心思,有時甚至頗為費力,但得到樂趣;我們從與人來往和愛護家庭得到樂趣;這些都是愉快知覺。我毫不懷疑這些慣性或經常的愉悅,對大多數知覺生物而言是樂多於苦,雖然有時受苦很慘。這些苦楚與自然選擇的信念頗為匹配;自然選擇這個動作並未做到完美,但還是讓物種在奇妙複雜和改變中的環境為生命而戰時,選出成功者。
沒有人會質疑世上有太多苦難。一些人試圖以人類作為解釋,想像這是為了改善人類的德行。但世上人類的數目與全部其他知覺生物的數目根本沒得比,而這些物體受極大苦難,沒有任何德行改進。對我等之有限思維來說,上帝可創造宇宙,威力無窮,知識廣博,是全知全能,若說上帝的仁愛不是無限,這違反了我們的理解,然而任由千萬低等動物無窮無盡受苦有什麼好處?我認為這舊調重彈謂受苦違反有智慧的造物主這說法強而有力;只能解釋為如上文所述,這種受苦是符合所有生物經由變異和自然選擇而發展的觀點。
現今最常見的「智慧上帝存在」論點,衍生自大多數人經歷過的深層內心信念和感受。但無可置疑,印度教徒、伊斯蘭教徒和其他人也可以依相同的論點,擁護單一或多個神,或如佛教徒般認為沒有神。還有許多野蠻部落信奉的,依我們的真理來看不能稱之為神者,他們信奉精靈或鬼魂,正如泰勒和斯賓塞7)曾指出這種信仰是因何而起。
以前,我被上文提到的感覺引導(雖然我不認為我有強烈的宗教感情),堅信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滅。我在《日誌》記述我站在壯觀的巴西森林,「心中充滿無以復加的驚奇、欣賞和虔誠的感受。」我記得很清楚我的信念是人的肉體除了呼吸之外,還有其他。但如今最宏觀的情景不會引起我有這些信念和感受。可以說我像變成了色盲,而其他人普遍相信有紅色,使我現在喪失的知覺沒有絲毫的實證價值。如果所有種族的所有人都有內在的信念相信存在一個上帝,這論點可以成立,但我們知道實情遠遠不是如此。因此我不認為就現實而言,這些內在信念和感受有任何實證的分量。以前使我感到激動,又與信仰上帝有緊密關連的宏偉情景,本質上與所謂崇高感覺沒有多大分別;無論要解釋這感覺的發生是如何困難,也不可能當作是「上帝存在」的論點,也不會超出音樂激發強大但模糊的類似感受。
談到永生8),沒有什麼告知我這信念是如何強烈和幾近是直覺,因為大多數物理學家現在相信太陽以及所有行星終會變冷,低溫使生命無法再延續,除非有一些龐大物體衝向太陽,令太陽獲得新生命。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人會比現在更為完美;在如此漫長和持續的緩慢進步之後,以為人類和其他知覺物種注定會全部滅絕,這種想法是不能容忍的。對於那些完全相信人類靈魂不滅的人,世界被摧毀看來並非那麼可怕。
「上帝存在」這信念的另一源頭是關乎理性而不是感覺,我覺得這較為有分量。這是源於很難或是甚至不可能設想這龐大和奇妙的宇宙,包括人類及其回顧過去和遠眺未來的能力,作為隨機或必然的結果。當我如此反思,我覺得有必要尋找在某程度上類似人類智慧思維的「第一因」;我值得被稱為是有神論者。
依我的記憶所及,當我撰寫《物種起源》時,我對這個結論9)有強烈信念,其後隨著許多波動變得越來越微弱。但疑慮油然而起:我全面相信人的思維是從最低等動物的腦袋發展而來,當人作出如此宏大的結論時,是否可以信任?我們覺得是必須的因果關連的結果,是否可能只是視乎承傳得來的經驗?我們也不可忽略經常諄諄教導孩童信仰上帝,會對還未完全發展的腦袋產生如此強烈以及可能是承傳的效果,要他們揚棄對上帝的信仰,猶如要求猴子揚棄對蛇的本能恐懼和憎恨10)。
我不假裝對這深奧難解的問題有任何答案。萬物之源的神秘,不是我們可以解答;我樂於成為「不可知論者」。
人要是對人格化上帝和未來果報不能肯定或沒有信心,依我所見,這人的人生準則只是追隨最強烈、或是在他看來是最有好處的衝動和本能。狗兒就是如此,但只是盲目如此。人會思前想後,而且衡量他的各種感受、欲望和記憶。然後他發現,依據所有智者的判斷,最大滿足感是源自某些衝動,即是社交本能。如果他為別人的好處而行動,他會得到同伴的讚許,得到共同生活的人鍾愛;後者無疑是世上最高的愉悅。他逐漸不能忍受服從感官狂熱而不是較高層次的衝動;習慣之後,這些衝動幾乎可稱之為本能。有時他會理性地拒絕依循他人的意見,為此得不到對方的讚許,但他會欣然滿足於知道他是依循內心深處或良知的指引。──就我個人而言,我相信我是穩步追隨和獻身於科學。我並沒有犯大罪而覺得自責,但時常懊悔沒有為人類多做好事。我唯一的差勁藉口是健康和精神欠佳,從一個題目轉移到另一個頗有困難。我可以想像把全部時間投入慈善會有多大滿足,雖然這會是較好的處世之道,但我只做到強差人意。
我11)的後半生較為不尋常舉動,莫過於推廣懷疑精神或是理性主義。在我成婚之前,父親告誡我要小心隱藏我的疑心,因為他說他知道這為已婚人士帶來的無盡煩惱。婚後一切美滿,直到丈夫或妻子健康轉壞,然後有些婦女疑心丈夫能否得到救贖因而感到不安,丈夫也因而苦惱。父親又說他一生只認識三位抱無神論的婦女;要記得他閱人無數,又有非凡能力贏得對方的信任。我問那三位婦女到底是誰,他只好承認其中一人是小姨Kitty Wedgwood;他沒有確實的證據,只是憑著最模糊的跡象,再加上信念認為這頭腦清醒的婦女不可能是信徒。在我熟悉的小圈子中,我知道有幾位太太的信仰不比她們的丈夫強很多。父親時常提到一項無法反駁的爭議:Barlow太太是老婦人,疑心父親不相信正教,希望改變他的信仰:「醫生,我知道口中的糖是甜的,同樣的,我也知道我的救世主是存在的。」
書評:《達爾文傳》
書名:Darwin
作者:Adrian Desmond and James Moore
出版:Warner, N.Y.
平裝808頁 1992 $35
達爾文在1859年出版《物種原始》,書裡面提到的演化理論,是十九世紀科學的革命性觀念,但卻遲遲才傳到中國來。1873年,萊爾(Lyell)的《地學淺釋》裡譯作「兌爾平」;1898年嚴復譯赫胥黎(Huxiey)的《天演論》叫作達爾文。這本書裡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字眼,變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口頭禪,因為嚴復在書上的註解,特別強調斯賓塞(Spenc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於是許多人把它當作政治口號而已。
《物種原始》本書遲到1919年才經馬君武譯成中文(六○年代北京另有新譯本,筆者沒見過)。達爾文的天擇學說(Natural Selection)可算是驚天動地的,於是大家對達爾文本人也很感興趣:究竟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怎麼會在那個基督教的社會環境中,能突破傳統地提出這種革命性的觀念?達爾文的傳記,最早是他為子孫寫的自傳,在1887年出版,其中他對宗教的懷疑部分,都被家人刪去,到1960年代才補回來。達爾文死後,傳記出版不間斷,多年來至少有12種版本(不知已有中譯本?)1959年,《物種原始》百週年紀念,歷史學者才注意到,達爾文是鉅細靡遺地寫筆記的人;多年來存在他家,沒人過問。從這些筆記裡,可以知道他思考的途徑,以及那天他肚子不舒服、頭痛、嘔吐,甚至每天晚上與夫人玩雙陸棋(Backgamon),一生六千局的成績,這類專門研究達爾文的報告,已經多到成為一種企業(Darwin Industry)(科學史的其他三大企業是:牛頓、愛因斯坦及佛洛依德)。
最新出版的這本《達爾文傳》,就是從這個企業整理出來的結果,除描述達爾文的經歷之外,特別襯托出他週遭的社會及生活環境。當時的急進分子,所出版的非主流報章書籍裡,都已經用演化眼光來說明社會的發展,尤其對英國國教所把持的社會組織提出責難。達爾文在其中耳濡目染地對拉馬克(Lamarck)式的「進化」模式非常熟悉。他異於拉馬克的創新,是指出演化並不是生物因環境壓力而自動改變以適應,他認為生物代代之間常有變種,當環境改變,自然地把不適應的物種淘汰掉,能適應的變種則以級數地增加下一代,於是有新種起而代之。本書最詳細的部分是他的生活細節,而達爾文的學術內容,則簡化太多,令人可惜。
達爾文是富有的醫生世家,祖父是工業革命時代,瓦特、化學家普利士利及瓷業大王魏吉伍德(Wedgwood)等人的好友,寫過一篇贊同萬物同宗,帶有演化概念的Zoonomia。母親是魏家女兒,他在1809年出生,排行老五,次男(按Sulloway研究講法,提出革命性科學觀念的,都不是出生排行老大!)家裡傳統信仰是一神論(Unitarian),這在英國的三位一體(Trinity)宗教社會中,算是個例外。小時候他跟哥哥在家裡作化學實驗,同學叫他「氣體」(Gas),且在外祖父的瓷廠裡體會到製造業的內涵。父親要他去愛丁堡學醫,他在那兒接觸到演化及唯物的觀念。不過,他對醫學沒興趣,於是轉到牛津改學神學,準備將來作個鄉下牧師(country parson)。
他熱中於採集昆蟲、騎馬、打獵,跟博物學家亨茲羅(Henslow)特別接近,經常隨著地質前輩賽吉威克(Sedgwick)去探看地質。就在地質工作之後,他接到亨茲羅的來信,介紹他去獵犬號測海艦,到南美及全球周遊五年。一路暈船中(延伸到一輩子的肚子不舒服?),看到各地動植物,種類相似而不同,於是對物種起源的問題特別注意;回倫敦之後,整理出版研究報告。他常常跟他哥哥的急進派朋友相聚,對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膨脹比食物增產為快」理論,耳熟能詳,於是在1838年就悟到物種變異的天擇理論,開始寫在筆記上(達爾文筆記、草稿都在最近整理成書出版),但悶在肚子裡,不敢發表。他曉得純物質性的演化論,在當時科學界都由權威教會把持的社會裡,一旦公布,將遭到嚴厲的唾罵。於是在地質學會中,台上演講人正天花亂墜地用生物適應自然的功能,來讚美上帝造物之妙,而台下在筆記上寫了責難連頁,並以演化論來解釋同一現象的達爾文,卻坐在那兒不動聲色!莫非是因為他得借重這些權威人士的支助,好在科學界爭立足之地,所以心理壓力奇重,導致嘔吐、頭痛而抱病終生。
不久,他跟信教虔誠的表姊Emma結婚,然後搬到倫敦南邊的Down村隱居。父親給他不少資金及不動產,儼然鄉紳牧師身分(Squire parson)。他一共生了十個孩子。
達爾文在1842年才把演化論寫成短文,過了兩年,擴大成230頁,並吩咐夫人在他死後,請好友虎克(Hooker)整理出版,之前沒跟任何人透露半點消息。達爾文到處跟博物學者、家畜及園藝專家聯絡,收集與物種變異有關的資料,家裡成為博物學界的彙集中心,並且養鴿、種植物等。本書就是達爾文博物研究與家庭生活的詳細寫照,書裡的用詞遣字故意採用他筆記、書信及當時(十九世紀)報章上常用的字眼,因此讀起來有點生疏,卻相當有趣。
他的女兒十歲久病而逝,弄得他心情沮喪,從此對基督教失去了信心。自己生病時,卻相信當時的偏方,用冷水浴來治療,於是一直舊病纏身,時好時壞。他心理上的畏避,社會輿論的不適合,使他把演化論埋了20年,只在最先告訴過虎克:「好像承認殺了人一樣」,後來也有幾個好友知道。早在1844年,倫敦出現了一本《造物自然史之遺跡》,用拉馬克的演化論,說上帝造物之後,訂了個演化律,讓生物自動一代代地改變而適應環境,此書當然引起博物學界群起而攻,達爾文因而更不敢發表。後來他花了八年工夫研究甲殼動物cirripedia的分類及構造,得了皇家學會的學術獎。再經萊爾、虎克的催促,從1855年起開始把演化論寫出11章的草稿。妙的是,在馬來亞的華勒士,於1858年同樣地悟到了天擇原理,一古腦兒把論文寄給達爾文。他收信時為之一呆,「好像看過我1842年的稿子而寫的摘要似的!」逼得達爾文匆匆寫出一本500頁的通俗博物書《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種原始),沒附參考資料就出版,一千多本頓時銷售一空,其後一共出了六版之多。
1860年後的達爾文,已是專業科學界的前輩權威,演化論經這些年輕後輩的宣揚,普遍地為生物學界所接受。他不斷地出書,擴張演化學說的領域,尤其在《人本》(The Descent of Man)一書裡,肯定了人與猿猴本是同宗。他一直住在鄉下,慕名訪客相當多,生活卻像機械式地規律化──忙著著作、養病、生孩子、管理投資。達爾文相當富裕地在1892年逝世!本來要埋在村裡,卻因年輕當權派朋友們的推崇,把這已經不信教的演化論者,抬到西敏寺,埋在牛頓旁邊。
這本新傳記,把他當時的家庭及社會,講得很親切,如臨其境。但可知達爾文其實是個很保守的鄉紳,一心要維持當代的階級及社會結構,「物競天擇」說,更是無限制資本主義社會的明朗反映。
資料來源
「親愛的Frank:
我極為希望刪去《自傳》的一句;無異部分原因是因為你父親認為『全部德行的成長是演化而來』這說法令我感到不安,也是因為這句子出現時帶來一種衝擊,無論是如何不公正會引起肇端:以為他認為全部精神信仰都是不能超越承傳而來的愛惡,一如猴子怕蛇。
我以為這說法的第一部分如省略猴子和蛇的例子,可以消除這出言不遜的方面。我認為不需為省略而諮詢William,因為這不會改變《自傳》的大意。如可能的話,我希望不要令與你父親情誼深厚的宗教朋友感到痛苦;我想到這句子會如何打擊他們,即使是開明一如Ellen Tollett和Laura、Sullivan上將、Caroline嬸嬸等人,甚至以前的老傭人。
E. D.」
劍橋大學出版社在1904年發行由Henrietta Litchfield撰寫的《達爾文夫人Emma Darwin》私藏版有收錄這函件;John Murray的1915年公開版本省略這函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