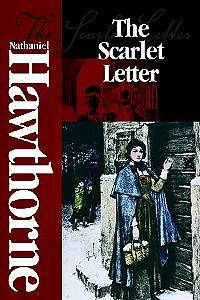本帖最後由 dior13dior13 於 2015/1/31 01:09 編輯
[聖經與文學]
穿透黑暗的愛與恩
--論霍桑的《紅字》
作者:郭秀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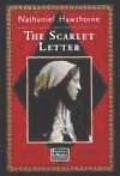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壹書一章9節)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社會在殖民兩百多年之後,歷經各種新舊思想的激盪與變動,終於在文學園地開花結果,一部部經典名作幾乎同時孕育而成。其中包括:史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1852),藉著黑奴悲慘的一生探討奴隸解放議題;崇尚個人絕對自由的超驗主議者愛默生,出版了他的思想鉅著《代表性的人間肖像》(Representative Men,1850);梭羅發表他的古典隨筆《湖濱散記》(Walden,1854);惠特曼劃時代的詩集《草葉集》問世(Leaves of Grass,1855);麥爾維爾則寫下美國文學史上的曠世經典《白鯨記》(Moby Dick,18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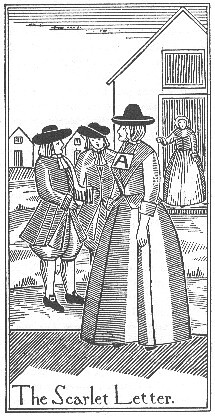
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正是在美國文壇這樣豐收的年代,於1850年寫出使他屹立世界文壇的《紅字》。霍桑在這部描寫「人性的脆弱與悲傷」的小說中,融入影響他個人極為深遠的清教徒遺傳,深刻剖析罪的意識對身心靈的影響、尖銳地批判已經淪為律法主義的清教精神、探討個人在自由與權威中的掙扎、赤裸裸地呈現人性中的愛恨糾葛。為此,霍桑被認為是美國文學史上浪漫小說和心理分析小說的開創者。

人性的脆弱與悲傷
《紅字》的舞台架設在1642年的波士頓殖民區,比霍桑所處的年代早了兩個世紀,正是他的清教徒祖先踏上麻州的年間。故事第1章從「獄門」的背景開場,霍桑在下面這段精彩的描繪中,似乎預告了小說的重要主題:
新殖民的建設者,無論他們原意是怎樣計劃著人類美德與幸福的烏托邦,然而總是從一開始,便在實際的需要中,認為一定要劃出一部份處女地作為墓地,另外劃出一部分作為監獄的地基。……在這片土地上這麼早就產生了文明社會的黑花--牢獄。但是在門口的一邊,幾乎就生根在門檻上,有一叢野薔薇,在這六月的時光,綴滿精緻的寶石般的花朵,使人想像,當囚徒進門或當被判決的犯人出來受刑的時候,它對他們呈獻出芬芳和嬌媚,藉以表示在大自然的深胸裡,對於他們還有憐憫,還有溫存。(頁75~76)
牢獄所象徵的罪惡、墓園象徵的死亡、薔薇象徵的希望,正是交織成整個故事情節的基本元素。故事的整體發展,雖然環繞在慘澹、陰暗的氛圍之中,卻隱隱透露出一線曙光。
故事在第2章就切入情節核心,女主角海絲特‧白蘭從這道陰深的獄門走了出來,手上抱著三個月大的嬰孩珠兒。海絲特的胸前,繡著一個腥紅的A字,四周還鑲上美麗的金線。她因通姦罪入獄,但她拒絕洩露孩子的父親是誰,於是被判站在絞刑臺上示眾三個小時,並得終生佩戴那個恥辱的標記。海絲特失蹤多年的丈夫,此刻悄然出現在旁觀的群眾之中,身材略顯畸形的老學究,這時化名為精通醫術的羅格‧齊靈窩斯醫生。他威脅年輕的妻子對他的身份保密,並發誓一定會找出那個藏身在黑暗中的共犯,意圖對他施加報復、使他的靈魂滅亡。

鎮上有一名頗受人敬重的青年牧師,叫亞瑟,丁梅斯代爾,他是海絲特的牧師,齊靈窩斯選擇他作為自己的精神導師。牧師當時身體狀況日益衰弱,一旦遭受點驚恐或意外事件,就會習慣性地將手攏在心上,臉色會驚惶地泛紅變白。他後來接受會眾善意的安排,邀請老醫師同住,接受他的治療。故事一直進行到第10章(全書共24章),齊靈窩斯和讀者才赫然發現青年牧師的秘密--他的胸前也有一個血紅的A字。霍桑並沒有交待這個嚇人的標記,是隱喻式的,還是實際烙在牧師的肉體上,使得這部帶點偵探意味的浪漫小說,更添幾許神秘氣氛。
清教倫理與浪漫主義的衝突
在這部大約十五萬字的小說中,霍桑寫了一篇三萬多字的楔子,名為「海關」,交待他怎樣獲得「紅字」的歷史殘存文件。大多數中譯本都將這篇文字刪除,認為與小說關係不大。不過,近代學者多數認為「海關」的序言,是解讀《紅字》的關鍵。
霍桑在這篇序言當中,細數他的譜系淵源。在移民到麻州撒冷城(Salem)的霍桑家族中,他特別提到隨身攜帶著聖經和寶劍的威廉‧霍桑(William Hathorne),他是一名法官兼教會首領,在1662年曾經嚴酷無情地逼迫貴格會的婦女。他的兒子約翰‧霍桑,繼承了這種迫害人的稟性,在1692年一樁審判異端的「撒冷城驅巫案」中,扮演主導的角色,處死十九人。霍桑為祖先沾滿血腥的殘酷行為,感到羞恥,他認為霍桑家族的敗落,實在是上帝的詛咒。霍桑甚至在入大學時,在自己的姓氏上加了一個w字母,以示和祖宗有所區別。
另一方面,霍桑在序裡將讀者拉回他所處的時代,追述多位文壇友人。他曾經在愛默生的影響下,加入「理想農莊」,生活了三年,體驗到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他述及自己怎樣在華爾騰湖畔與梭羅談論自然;曾經在朗費羅家的爐火旁受到詩情的陶冶;麥爾維爾更一度是他最好的知己。
在這篇序言中,霍桑以相當負面的筆調,描繪他任職三年的撒冷城海關。他為了生計,不得已中斷自己多年的寫作生涯,於1846年出任海關首席檢查官,處在一群愛打瞌睡、沒精打采的老吏中間。不幸由於政權交替,霍桑遭受革職。在妻子的鼓勵之下,霍桑重拾自由的詩魂,靠著妻子的一點積蓄過日子。只花了一年時間,就寫下《紅字》這部傳世的心靈羅曼史。他稱自己的作品為「一個上了斷頭台的檢查官的遺作」,丟了官卻意外使自己被禁閉的心靈獲得重生,雖然他豁達地寫道:「祝福我的朋友平安無事!寬恕我的敵人!因為我已處在寧靜的天國。」(頁73)不過,還是有學者認為霍桑藉著「海關」一文,一方面感懷以寫作為生的辛酸,同時也攻擊罷免他的政客。「海關」中老朽、僵化的氛圍,在紅字的清教徒社會清楚呈現。
霍桑對於清教徒主義,其實並沒有全然摒棄,他仍然不時以自己的優良血統與信仰為傲。清教徒本來就是一群擁有夢想的革命家,為了掙脫英國國教派的種種限制,乃至遠渡重洋到新大陸建構理想國,只是人性墮落的本質,加上政教合一的弊病,很快使一群被逼迫者,成為更嚴苛的立法者和迫害者。但是,霍桑也沒有全然擁抱當時文壇流行的超驗主義。他的世界觀相當複雜,一方面深受這種崇尚人道與自然的樂天思維影響,一方面又信仰悲觀的加爾文主義,即接受絕對的惡以及人性的全然墮落。也因此,孕育出這部充滿歧義性(ambiguity)與反諷性(irony)的深邃作品。
A字的歧義性
 A字想當然耳代表「姦淫」(adultery),這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社會,設計出來對付海絲特的恥辱標記。不過隨著海絲特展現針線絕活,以及刻意過著最儉樸的生活,卻樂善好施,她逐漸贏得居民的敬重,他們漸漸視A字為「能幹」(able)的表記(頁196),甚至「在他們的心目中,那個紅字已含有如修女胸前十字架的意義了」(頁197)。霍桑說海絲特犧牲自己的享樂,積極行善,「恐怕並不是純真堅決的懺悔」,是一種「深深的謬誤」(頁112)。霍桑所指的謬誤,應該是海絲特想要靠行善、積功德而贖罪的心態。海絲特曾問牧師:「用善行來補救來保證的悔悟,會是不實際的嗎?」(頁231)靠工作得救,正是律法主義下的清教徒所具有的傾向。因此,霍桑寫道:「那個紅字還沒有完成它的職務」(頁201)。 A字想當然耳代表「姦淫」(adultery),這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社會,設計出來對付海絲特的恥辱標記。不過隨著海絲特展現針線絕活,以及刻意過著最儉樸的生活,卻樂善好施,她逐漸贏得居民的敬重,他們漸漸視A字為「能幹」(able)的表記(頁196),甚至「在他們的心目中,那個紅字已含有如修女胸前十字架的意義了」(頁197)。霍桑說海絲特犧牲自己的享樂,積極行善,「恐怕並不是純真堅決的懺悔」,是一種「深深的謬誤」(頁112)。霍桑所指的謬誤,應該是海絲特想要靠行善、積功德而贖罪的心態。海絲特曾問牧師:「用善行來補救來保證的悔悟,會是不實際的嗎?」(頁231)靠工作得救,正是律法主義下的清教徒所具有的傾向。因此,霍桑寫道:「那個紅字還沒有完成它的職務」(頁201)。
這點,在長期不肯認罪的丁梅斯代爾身上,也可以看見。對於這位青年牧師而言,A字首先指涉了他的姓名「亞瑟」(Arthur),也象徵他為了事業「野心」(ambition),過著假冒偽善的生活,沒有勇氣承認真相。霍桑藉牧師之口寫道:「他們畏縮不敢把自己的黑暗和污穢展現在人的眼前;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再有善行;而過去的惡行也無法用良好的服務來贖償了。」(頁166)由此可以看出,牧師也是錯誤地想靠作工得救,他加倍地敬虔苦修,講道充滿能力,即使最後已經計劃偕海絲特母女逃亡,他都還期待著,能夠在講完慶祝選舉的道之後,再完美地結束他的牧師生涯。只是,表裡不一致,終究撕裂了他的身心。
對齊靈窩斯和清教徒社會來說,A字代表了「老化」(aged)與「祖先遺傳」(ancestry),最終象徵殘酷的報復(avenge)。齊靈窩斯為了復仇,隱姓埋名,他「寧願把他的姓名從人類的名冊上取消掉」(頁150)。霍桑描寫他左肩比右肩高出許多,象徵他在知識與靈性的發展上不成比例。他被塑造為惡魔似的角色,因他犯了罪中之罪,越權踏入上帝的領域,想要使對手的靈魂滅亡。不過,他最後也良心發現,將遺產留給與他沒有血緣關係的珠兒。
清教徒社會宣稱珠兒是惡魔生的,海絲特卻堅稱這是上帝賜給她的寶貝,所以為她取名珍珠(Pearl)。當人們要搶走珠兒,海絲特叫道:「她是我的幸福!然而也同樣是我的苦惱!珠兒叫我活在世上!珠兒也給我懲罰!你們沒看見嗎?她就是那個紅字。」(頁144)珠兒既是活的紅字,那麼她所代表的精神是什麼呢?這點相當難以掌握,或許珠兒是「天使」般的角色(angel),挽救海絲特的靈魂免於滅亡,若沒有珠兒,她可能早就自我了斷,或遠離人群、躲進曠野。珠兒惹人憐愛的容貌和不受馴服的天性,也可能象徵浪漫主義所高舉的自然,珠兒曾經為自己編織了一個綠色的A字。或許霍桑要我們正視人性的情欲,是極為自然的天性,因此不是鮮紅而是新綠。不過他在海絲特佩戴紅字示眾時也同時寫下:
在社會尚未腐敗到目睹這種場景不致戰慄卻反而微笑之前,這種場景裡並非不存著敬畏,而這正是一個人目睹恥辱與罪惡的光景時擺脫不掉的感覺。(頁84)
今日墮落的社會,人們傾向接受「只要有愛就沒有罪」,相較之下,霍桑、或海絲特或亞瑟牧師,他們保守得多,他們看待通姦是軟弱、是罪惡、是恥辱。代表自然精神的曠野,在《紅字》全書一直是相當負面的意象,未馴服的處女森林地,代表寂寞與疏離,是邪靈出沒的領域。
超越一切的恩典

雖然,海絲特多次任自己的精神在荒野徘徊,她的命運使她遠離人群,使她趨向成為一個自然人,但是,霍桑寫道:「這些做了她的教師,而且是嚴峻粗野的教師,他們一面使她堅強,一面也教給她許多錯誤。」(頁241)
七年來的法外生活磨練,使海絲特有勇氣提出逃亡計劃,因她不忍看牧師被齊靈窩斯折磨至死。然而,故事從「一片陽光」的第18章之後,情節急轉直下,迷惘的牧師終於看清:他不能逃走,他必須真誠地面對自己、面對事實,更重要的是,他發現神除了是公義的神,祂更有憐憫和恩典,祂是愛的神。
因此,在第23章「紅字的顯露」,丁梅斯代爾講完道後,勇敢地招呼海絲特扶他步上刑臺,他說:
上帝在上,他是那麼可怕又是那麼慈悲,在這最後的一瞬間,為了我自己深重的罪孽和悲慘的痛苦,他已恩許我實踐七年前我自己畏縮避開的事。(頁296)
齊靈窩斯企圖攔阻他的認罪悔改,牧師對他說:「感謝那領我到此地來的上帝!」然後轉身對海絲特微笑,悄悄地說:「這不是更好嗎?和我們在森林中曾經夢想過的事比起來?」牧師以顫抖的聲音向會眾喊道:
請看我在這裡,一個世界的罪人!總算是到了這麼一天!總算是到了這麼一天!我終於站到我七年前應當同這個婦人一起站立的地方了,就是這個婦人的膀臂,在這可怕的瞬間,用它小小的氣力,攙我爬到這裡來,支持我不致撲面倒在地上!(頁297~298)
牧師和珠兒親吻,破解了她所受到的符咒,「珠兒,做為一個痛苦的使者,對於她母親的使命,也已完成了。」(頁299)牧師在海絲特的胸前斷了他的氣息。
霍桑以最後一章交待了其他角色的結局。齊靈窩斯在喪失生存的意義之後,很快死亡,將一筆可觀的遺產留給珠兒,使她在異?享受著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而海絲特在消失多年之後,又回到新英格蘭半島邊緣上的老舊茅屋,繼續戴著A字過她懺悔的生活,成為女先知般的角色。她死後葬在牧師的墓附近,兩座墳雖然隔著一段空間,卻合用一個墓碑,全書就結束在這行碑文:
「一片黑地上,刻著血紅的A字。」(頁307)
結語:一部真正的基督教經典
事實上,霍桑對書中四個主要角色和清教徒社會,都是褒貶愛惡皆有,再加上現實的「海關」與虛構的小說之間的交錯,使得《紅字》充滿了雙元性(bivalence),造成評論家對這部作品的詮釋,產生許多衝突。多數人認為海絲特是真正的英雄,稱讚她勇敢的愛情和對自由的追求,視丁梅斯代爾的死亡為宿命式的悲劇。近代學者更喜歡以後現代學者的論述方式,如德希達與傅柯等的閱讀理論,重新探索《紅字》的文本,主張其意義不可尋得。其實,筆者相信任何一個閱讀《紅字》的基督徒,很自然會聯想到聖經中「行淫的婦人」故事(約翰福音八章1~11節),並與之對照。耶穌在那段經文強調祂救贖的使命,指出罪的共通性和普遍性,應該使人類產生同情、彼此相愛。霍桑在寫作《紅字》的時候,不可能不受到聖經和正統加爾文神學的影響--「倘若沒有上帝的慈悲,無論是用言語,或是用標誌,任何力量都不能暴露出那可以埋葬在人的胸懷裡的秘密。 」(頁165)--評論家不應該忽視這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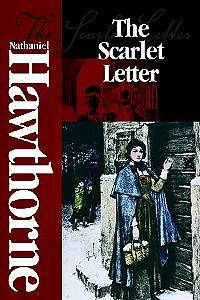
惠頓大學的文學教授李肯(Leland Ryken),讚揚《紅字》具備高度藝術技巧和完美的結構,頭尾兩章為序和跋,作者平衡地在開頭、中間和結尾(第2、12、23章)三處關鍵篇章,讓全書最重要的四個角色,一起出現在可怖的示眾刑臺。李肯指出海絲特所面臨的衝突,在全書發展到一半就已解決--她早獲得清教徒社會某種程度的敬重,他指出:
至此我們才發現《紅字》的主角並非海絲特,而是丁梅斯代爾。……整部作品的進展,是為了尋求丁梅斯代爾的得贖。……一部作品能否被稱為「基督教經典」,必須看它是否展示福音的核心信仰。《紅字》,誠如評論家(W. Stacy Johnson)所言:「是救恩的完整呈現。」(Realms of Gold, by Leland Ryken, p.153)
對於認信基督的霍桑而言,《紅字》的終極關懷,應該是在於作家以他卓越的「藝術」形式(artistic),為讀者創造了這部無與倫比的「贖罪」故事(atonement)! | 











 2010/7/17 02:00
|
2010/7/17 02: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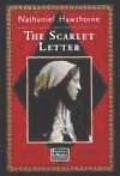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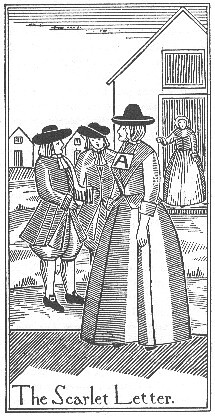


 A字想當然耳代表「姦淫」(adultery),這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社會,設計出來對付海絲特的恥辱標記。不過隨著海絲特展現針線絕活,以及刻意過著最儉樸的生活,卻樂善好施,她逐漸贏得居民的敬重,他們漸漸視A字為「能幹」(able)的表記(頁196),甚至「在他們的心目中,那個紅字已含有如修女胸前十字架的意義了」(頁197)。霍桑說海絲特犧牲自己的享樂,積極行善,「恐怕並不是純真堅決的懺悔」,是一種「深深的謬誤」(頁112)。霍桑所指的謬誤,應該是海絲特想要靠行善、積功德而贖罪的心態。海絲特曾問牧師:「用善行來補救來保證的悔悟,會是不實際的嗎?」(頁231)靠工作得救,正是律法主義下的清教徒所具有的傾向。因此,霍桑寫道:「那個紅字還沒有完成它的職務」(頁201)。
A字想當然耳代表「姦淫」(adultery),這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社會,設計出來對付海絲特的恥辱標記。不過隨著海絲特展現針線絕活,以及刻意過著最儉樸的生活,卻樂善好施,她逐漸贏得居民的敬重,他們漸漸視A字為「能幹」(able)的表記(頁196),甚至「在他們的心目中,那個紅字已含有如修女胸前十字架的意義了」(頁197)。霍桑說海絲特犧牲自己的享樂,積極行善,「恐怕並不是純真堅決的懺悔」,是一種「深深的謬誤」(頁112)。霍桑所指的謬誤,應該是海絲特想要靠行善、積功德而贖罪的心態。海絲特曾問牧師:「用善行來補救來保證的悔悟,會是不實際的嗎?」(頁231)靠工作得救,正是律法主義下的清教徒所具有的傾向。因此,霍桑寫道:「那個紅字還沒有完成它的職務」(頁201)。